1283年的冬天,大都城外几个身影缓缓走进刑场。

其中一位瘦削女子步履艰难,却格外坚定,她是欧阳氏,曾是南宋宰相文天祥的正妻,如今是元宫中的卑贱宫奴。
数日前,她接到消息,可以前往收殓丈夫尸体。
可当她颤抖着揭开丈夫遗体的衣襟,发现那片残破衣带上的手书时,泪水和悔意瞬间决堤。
后来,欧阳氏自尽,一位曾低首求生的女子,留下了最后的绝唱。

文天祥的手书写了什么?她为何要自尽?忠魂不屈
元大都一座阴冷潮湿、幽暗逼仄的牢狱中,一个中年男子披头散发地靠坐在墙角。
他面容憔悴,须发斑白,这个人,便是南宋末年的丞相文天祥。
自五坡岭兵败被俘,文天祥被押解至大都,至此度过了整整五年囚徒生涯。
五年,他每日所面对的,是铁锁加身、酷刑相逼,每夜所忍受的,是寒气入骨、梦魇缠身。
唯一不变的,是他那颗如磐石般的忠心。

忽必烈对文天祥这个人,最初是欣赏的。
他才华横溢,军政皆通,诗文俱佳。
一个中原士大夫最极致的模样,便是他。
他若能归顺,既可安抚汉人之心,又能增大元朝威望。
因此,自他被押到京城之日始,忽必烈便亲自下令不得草草处置,要“劝其为用”。
第一次招降,是由降宋的大臣来劝。
那些曾在文天祥麾下听命行事的旧臣,身着大元的官袍,冠冕堂皇地踏进牢房,口中却是劝其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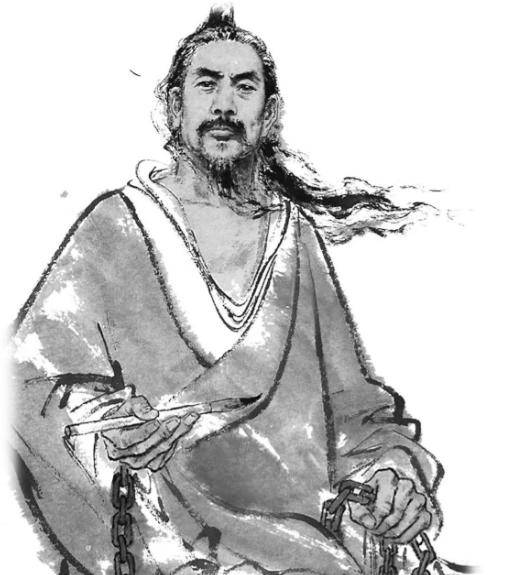
文天祥倚坐不动,只一言:“国破而不死,羞与为伍。”那几人面面相觑,最终只能讪讪而退。
第二次,是派他的亲弟弟文璧前来劝降。
血浓于水,兄弟二人从小一同读书、习武、同窗共砚。
可这一日,一个披枷带锁,一个锦袍玉带,牢门咿呀开合,两人四目相对,沉默如山。
年幼的女儿也曾来信,幼子不知什么是国破家亡,她只想让父亲安康。
文天祥终究在一片沉寂中提笔。
他没写“答应”二字,也没写怒斥之语。
他写的是:“痴儿莫为今生计,还中来生未了因。”

短短几句,却道尽了一个丈夫、父亲的隐忍和诀别。
他告诉女儿,要好好做人,告诉妻子,不必为他愧疚,他知道,她们身不由己。
五年来,他不曾为敌人落泪,却为这封信几欲断肠。
之后的日子,忽必烈失去了耐心。
他不再派人,而是直接将文天祥关进死牢,狱卒不再客气,白日鞭打,夜里冻饿。
更有甚者,在他腿骨上狠砸数锤,生生将其打断。
那一日,文天祥疼得几近昏厥,他咬破舌尖才勉强让自己保持清醒。
他不愿昏迷,因为一旦沉睡过去,连死的念头都不能自主掌控。

文天祥倚着墙壁,用破衣裹紧双腿。
膝上的羊皮纸已被翻阅得边角卷起,笔墨是他用焦炭混着水写成的。
他不再写给皇帝,也不再写给百官,而是写给这个世界,写给后人。
他把血泪和信仰熬成了诗,在《指南录》《吟啸集》里留下了一个囚徒的忠魂。他说:
“臣心一片磁针石,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
这些文字,不为表忠,只为存证。
即便亡国,尚有余烬,即便身陷牢笼,尚有骨气。

忽必烈终究按捺不住,他亲自来到牢前,说:
“若你肯效忠我,我便封你为丞相,统领百官,荣华富贵,一生不尽。”
牢中人微微抬头,满脸血污却仍清晰吐出一句话:
“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,只有一死,别无他求。”
这一次,连忽必烈也沉默了,他转身离去,不再回头。
帝王惜才,却更重江山,他不能为一介不屈文臣毁了自己的威信。
行刑前,文天祥索来纸笔,他知道,这是最后一次写字的机会。
他摊开布衣衣襟,在那上头一笔一划,写下字句。

字字铿锵,如雷击石,那不是遗书,是绝笔,是一个士人用尽气力的呐喊。
天光未明,文天祥跪拜南方,挺胸走上刑场。
他终究没有选择生的苟安,而是选择了死的坦荡。
他不曾问世间是否记得他,只问自己是否无愧于心。殉国路上
时间回到1278年冬,五坡岭风声猎猎。
文天祥匆匆咽下口中还未吞完的饭食,手中紧紧攥着一包龙脑。
那是一种烈性毒药,是他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道退路。

他并不奢望突围成功,只盼自己能在落入敌手前完成殉国,这是他作为南宋丞相、忠臣最后的使命。
可天意弄人,元军突如其来,他未及逃出山岭便被擒。
龙脑入口,他满以为死期将至,却不料毒性缓慢、未能立时毙命。
他便在山间地面上抓起污泥脏水强灌入腹,只求催毒发作。
可这番折磨,命却未断,龙脑和污水只令他剧烈腹泻,却救回了一条命。
当文天祥再次醒来,已在元军的囚车中。
他抬头望见天色灰白,耳边是元兵咒骂与马蹄声。囚车颠簸着向北驶去,每一寸路程,都是对他精神的拷打。

从此,文天祥开启了那场长达千里的北上囚旅。
他曾多次绝食,每一顿不食,都是对自身信仰的捍卫。
他一度拒绝进水八日,面容憔悴如鬼魅,连看守的士卒都以为他熬不过寒冬。
可他又一次奇迹般活下来。
命,像是死死缠住他,不让他轻易赴义。
更深一层的痛苦,来自于途中亲眼所见的崖山之殇。
押送途中,囚车驻留在海边,崖山战事刚落帷幕。
船舱狭小,角落一扇细窗,他斜靠在那腐朽的木窗下,目睹了震撼人心的场景。

海面茫茫,十万同胞的尸体随波逐流。
南宋军队与皇室、平民在海中成片沉没,或被元兵屠戮,或主动投海殉国。
一群群人不带哭喊,抱着孩童、携着长辈,一步步走入那没有归途的水里。
文天祥眼睁睁看着老臣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小皇帝赵昺纵身跃入波涛,那一跃,如一座王朝最后的旗帜坠入深渊。
整整一夜,他跪坐在舱中,口中含泪无语,只不断磕头朝南,额头敲得破皮出血。
那是对同袍的哀悼,对旧国的送别,也是对自己无法赴死的痛斥。

自此之后,他在囚车中再无睡眠,每夜都在昏暗的灯光下反复吟诵,用血泪凝成诗句。
他被送入元大都的死牢,他的腿早被狱卒打断,只能靠着残破木床勉强支撑。
他的饭菜里常混有沙土,他的衣衫冬夏如一,可他仍然,坚毅如初。
他以炭代墨,以石代笔,把千年文脉与血肉之忠写进了一页页粗糙的布帛中。
他说: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,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”
这是《正气歌》,更是他将忠魂寄予万物的誓言。
五年时间,他在地牢中写下五百余首诗,汇成《指南录》《吟啸集》等卷。

这些诗句不是吟咏山水,不是感怀春秋,而是一个囚徒面对亡国、苦难、死亡时,仍执笔如剑,丹心照汗青的见证。
他以诗传信,以字写志。
他不能上战场,却在纸上为大宋立起最后的旌旗。
他曾在诗中说: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短短十四字,横亘古今。
那不是高调的口号,而是他用血与骨雕刻下的誓言。
历史或许不会记住他曾吃过多少苦,但会记得他在灭国之后,还留下一身浩然之气,抵得住整个王朝的崩塌。

于是,当他被押至刑场的那一日,大都百姓私下传言:“此人不降,真乃天人。”
这是他最后的自白,也是留给天地间最后一份刚正。衣带绝笔
文天祥死了,这个南宋末年的状元宰相,终于在刑场上结束了他五年的囚徒生涯。
几日后,元廷破例宽恩,许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往收尸。
这是她失踪多年后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,曾经南宋宰相的夫人,如今却是宫中最卑贱的官奴,一身灰衣、布履、憔悴如影。

她缓缓走进刑场边的小巷,那里一具草席裹着的尸体静静地躺着,无人识得。
欧阳氏站在那具躯体前,沉默良久,然后缓缓蹲下,颤抖着伸出手,掀开草席的一角。
那一刻,时光仿佛冻结。
她看到文天祥的脸,眉目安详,仿佛仍旧活着,只是沉沉睡去。
即便死去数日,尸首却不腐,面色如生,这一幕让她一瞬间泪崩。
她并非不爱他,自从文天祥被俘,她便日日期盼,夜夜祈祷。
可她终究是女子,在那国破家亡、身不由己的命运中,她曾写信劝夫屈膝,只为能换来一家团聚的可能。

她知道那一封信成了他的心伤,也成了自己终生的羞耻。
而如今,他死了,却用死,将她曾经的劝降与懦弱一一洗净。
她轻轻翻开丈夫的衣襟,忽然发现,那破旧的衣带之上,竟然有墨迹犹新的字迹。
她擦了擦眼,低头细看:
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惟其义尽,所以仁至,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。”
这是他的绝笔,是用命换来的最后一段话。
字迹遒劲而不失温润,笔锋间仿佛仍带着他最后一丝体温。
孔孟之道,仁义为本。他一生读书为官,不为富贵,不为安乐,只为忠义。

他用死亡回答了这世上最后一个问题:“读圣贤书,所学何事?”
欧阳氏整个人僵在那里,一行行泪水悄然滑落,那是悔恨,那是自责,那是她此生无法偿还的愧疚。
她曾一度告诉自己:“若他能活,何妨低头?”
可如今她才明白,他活着,是为这“义”而生,不可轻辱。
她终究还是不懂他,直到他死,她才读懂他留下的那行衣带绝笔。
她将丈夫的尸体带走,一步一跪地走出刑场,将他葬于城郊荒地之中。
安葬当夜,她跪于祠堂之中,一夜未起。
翌日清晨,仆人推门而入,却见她身影轻悬于梁上,她用自己的方式,为那一封劝降书赎罪。
或许,她不是忠烈之士,却也是烈女之躯,她不是怕死,只是直到这一刻,才找到赴死的理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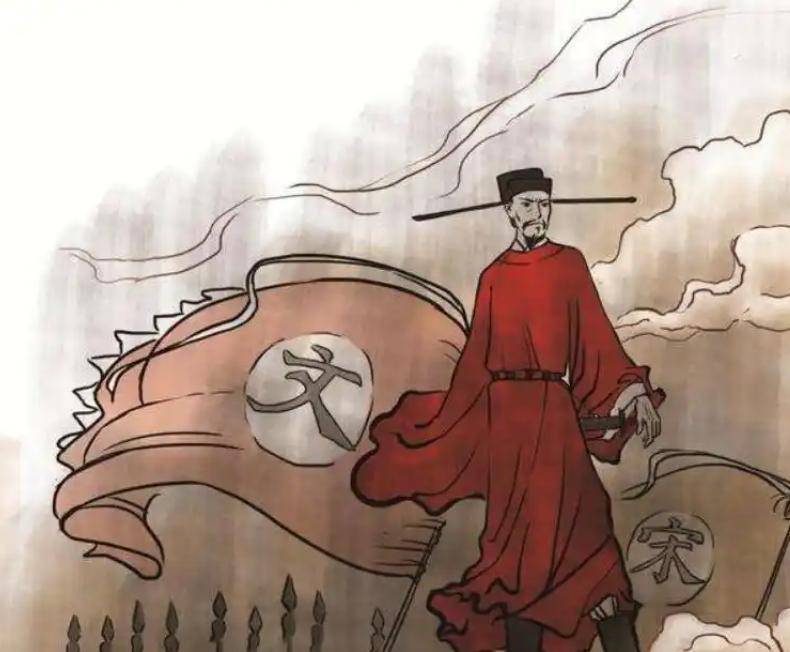
此后,大都再无欧阳氏之名。
人们以为她早已死去,或被遣返,或病亡。
可直到十五年后,文天祥的侄子几经辗转,竟在城外一座无名孤墓旁发现一个衣着朴素、鬓发斑白的老妇人,正为一座石碑擦拭尘埃。
或许,她不是那千古文章中的主角,但她用十五年,给自己赎了一个不该的劝降,也给世人留下了另一种忠贞的模样。
有人说,文天祥的绝笔《衣带赞》,是千古忠魂的绝响,而欧阳氏十五年的守墓,是这绝响之后,最温柔也最沉痛的回音。